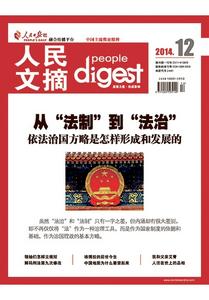
本文摘自:《人民文摘》2014年第12期,作者:李天綱,原題:《張學良和胡蝶:緣慳一面》
監禁中的張學良,有三個老師:曾國藩的曾孫曾約農教授教他中文,返臺的駐美外交官董顯光大使教他英文,臺灣浸信會周聯華牧師則專門為他講授《圣經》。據悉,三人中間,周牧師和張學良聯系最久,關系也最深。他為張學良和趙四小姐補辦了婚禮。張學良和趙四小姐晚年住在夏威夷,周牧師經常去探望。最后,周牧師還為張學良主持了葬禮。對于關系到當初上海坊間津津樂道的緋聞,即1931年“九一八事變”爆發的那一刻,張學良(1901年~2001年)到底有沒有在北平六國飯店和“絕代佳人”電影明星胡蝶(1908年~1989年)跳交誼舞?周牧師給出了真相。
周牧師回顧了一下事情的原委:“九一八事變”日本關東軍侵占東北后月余,天津的一份《庸報》披露說,當天晚上張學良不在沈陽,他在北平六國飯店和胡蝶跳舞!11月20日,南社詩人馬君武(1881年~1940年)義憤填膺,在上海《時事新報》上發表了《哀沈陽》二首。其一:“趙四風流朱五狂,翩翩胡蝶最當行;溫柔鄉是英雄冢,哪管東師入沈陽。”其二:“告急軍書夜半來,開場弦管又相催;沈陽已陷休回顧,更抱佳人舞幾回。”這位詩人是老同盟會的,他言之鑿鑿地說了這件事情,于是舉國嘩然。
張學良喜歡跳舞是真的,有女人緣也是不假,抽大煙更是公開的事,所以這種說法不脛而走。周牧師表示,“少帥”的聲色犬馬,在當時的道德觀看來,只是風流,并非惡疾,張學良可以承認。但是,馬君武把“風流”和“亡國”連在一起,他則不能承受了。張學良一輩子最痛恨《哀沈陽》,他在晚年接受唐德剛訪問時,仍然耿耿于懷,痛斥馬君武,決不承認當晚曾追著胡蝶跳舞。其實,他當晚是在北平中和戲院,攜趙四小姐和夫人于鳳至,陪著英國公使看梅蘭芳的《宇宙鋒》。
張學良拒不承認,胡蝶也在辯誣,按《胡蝶回憶錄》說,當天她隨明星電影公司一行在天津,潘有聲、張石川、洪深等人可以為證。胡蝶在《申報》上辟謠,明星影業公司證明,都沒有用。喜歡聽“紅顏禍國”故事的國人不相信,而且傳得更兇。有一次,張學良來上海,胡蝶曾求見“張副軍長”,說要當著上海報界的面說說清楚,張學良拒絕了,“那樣豈不更說不清楚?”
周牧師把張學良、胡蝶的公案在臺北延續下去了。20世紀60年代,胡蝶在港臺復出,拍了好幾部轟動的影片。息影之后的幾年,她住在臺北。當時,張學良雖說還是在監禁中,但他愿意見誰,當局還是會允許的。因此,臺北圈內都以見到“少帥”為榮。臺北是一個懷舊的城市,懷上海,懷北平,也不斷有人想撮合他們見面,看看戲外之戲。
臺北的社交圈子里公認,這個Mission(使命),只有周牧師才可以完成。有一次來機會了,老上海明星影業公司有一位胡蝶的御用攝影師,他的女兒在臺北辦婚禮,胡蝶出席。新郎父子都是浸信會教友,周牧師當然也應允證婚。兩位重要嘉賓,被安排在主桌上,座位緊靠,席間胡蝶說:“周牧師,求你一件事,你能不能夠請客,請我和張學良吃飯。我背了一生的黑鍋,卻從來沒有見過這個人。”周牧師答應試試看。周牧師也是一個很有戲劇感的人,他也很愿意看到這個故事的結局,回去真的和張學良說了。周牧師設計了輕松的口吻,說:“副軍長,猜猜我上禮拜和誰吃飯啦?”張學良:“我哪里知道你和誰吃飯,你認識那么多人。”周牧師:“是和胡蝶吃飯哎,你眼熱嗎?”張學良竟然湊趣地說:“好小子,你行啊!連我都還沒有見過她呢,你都和她吃過飯啦!”周牧師覺得有希望,就說:“那我請客你們倆人,大家一起會一會?”這時候,張學良馬上意興闌珊了,“算啦,不見也罷。”于是,最傳奇的“英雄與美人”還是緣慳一面,在臺北,在上海,還有在北平,他們都沒有見過面,更不曾“跳舞”。![]()



已有0人發表了評論